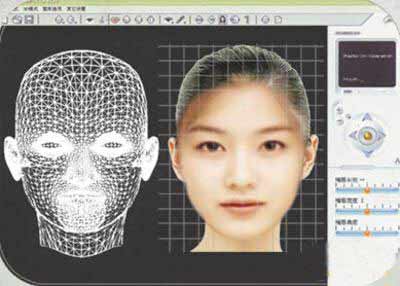���ʼZ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؎X����ˮ��Y(ji��)
���G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Ǵ�ػش��ĕr(sh��)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ĉ�ð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P(gu��n)�I�~���ʼZ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ʼZ犡���һ���L(zh��ng)ƪС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С�f��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º͵��@ӑ�ɵ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ܿ������ˌ��Һ��x�ߵ�ע�⣬����ˇ��(b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q��ng)?b��o)��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��ҾW(w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ҡ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Ϣī�E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D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؛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Ԓ���^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i��n)ϵ�ڶ���؛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؎X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}��С�f�Ī�(d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@��С�f�й⡰��ˮ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ϰٴΡ�С�f����ˮ���Ԟ锢���d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N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Ϣ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؎X�Ĺ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̓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̓��(g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߲����C��ˮ�^(q��)�h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͛]��һ��(g��)ʲô�]�_(t��i)�h��ɽ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Щ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]�_(t��i)�h�l(xi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ĻʼZ状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һЩ�й��{(di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ġ����g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ۺޡ��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ʵ®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ĺζ�������؎X���Vӛ�ߣ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ˮ�ǂ�(g��)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_һ��(g��)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װق�(g��)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x�ϵ��]�_(t��i)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K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}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˂�(g��)܊���g(sh��)�Z(y��)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ʼZ犡��е��]�_(t��i)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؎X��ˮ��Y(ji��)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ˮ�в��ɷָ��һ�}�����Ђ�(g��) �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҂�?c��)ھ�����٩�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؎X�ļ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ˮ���ؚ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ĕ�(hu��)���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o���ռ�����ˮ�ٿơ����T���˻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V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幫�����¹�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ս��S��ʧ��ͤ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q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ľ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ʲ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eɽ�����ˏ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؞�ʲô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�Ѿ��R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Ү�(d��ng)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ˮ�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ԭ�Ԟ������һ�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؎X�s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]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ݏU��ĵ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ؚ��߀�ô(g��)����Ů�o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؎X�ǂ�(g��)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ͨ�^�M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U���wԭ���ꡰ�U���w�wDz�ͻ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Ů��һ��ͺ��w�Ĵ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ʼZ犡���B�˝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�Y(ji��)���؎X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}��С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ᵽ��ˮ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2007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)���؎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e�k����Ʒ��ӑ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_(d��)�����Ժ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J(r��n)�飺��ˮ��Y(ji��)��ȫ���؎X����؎X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}��С�f֮�������ĉ���һ��Ӱ푣��c��Ƭ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؎X�ڡ��ʼZ犡��ĺ�ӛ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վ���Լ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f�����ִ���ҕҰ��Ĵ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̎�����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գ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f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r(n��ng)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@�ӵ�Ԓ��Ԓ���؎X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Ͳ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ӵ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͕�(hu��)�в�һ�ӵ�С�f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4��14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҅f(xi��)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и�(j��)����Ժ�P(gu��n)�ڡ�����֪�R(sh��)�a(ch��n)��(qu��n)�ա���Մ��(hu��)�g϶�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��f(xi��)����ϯ�Y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Ո(q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ϯ�^��һ�ѷ��١����Ρ��a��ֻҊ�@λ�Ї�(gu��)�ĉ��Ĵ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Ć̏S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ľ��ž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۾�һ�ɣ��ך�ʮ���?c��i)�ȣ����؎X��ͥ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ڡ��ʼZ犡��ĸ��M(f��i)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猍(sh��)�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؎X���һ˲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ݡ���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猍(sh��)�R��(b��o)���M(f��i)��(sh��)�~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١��Y�����F�ʹ�����֮ǰ����[�m���M(f��i)��(sh��)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؎X�f�����طA���ˣ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Ƿ�ͥ�����ֻ�܌�(sh��)Ԓ��(sh��)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һ��һ�ٵļ�ϯ���[������һƬ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Ŀ����һ��(ch��ng)���ʽ^���ġ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죬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ӳ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ۇ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ق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��ǰ���ϡ��ČW(xu��)�硷�s־���؎X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Ԓ�е�һ�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��ж�Ԓ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@ô�f�ģ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ɼ��ض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h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ܲ��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е�һ�О���r(ji��)�� ���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ؽ����˼��l(xi��ng)�ĠI(y��ng)�B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@ͬ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ᄵĹ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Ĺ�������Ƿ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(y��u)����Ʒ�ı�Ȼ�����Ҳ��ö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ҵ�ҕ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߉�Ǵ��ڵġ�
�����؎X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ȥ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Еr(sh��)�nj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Еr(sh��)�ǎ����Ӱ���Mȥ�w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f���(qu��n)�Ҍұ�Ӱҕ��˾�I�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Ƭ�˶�ҪՈ(q��ng)����ɽһ��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ɳ��ˣ��џΏ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Ƥ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՛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ö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Ͱ��ո��Ե���־�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˱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̫��ɽζ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Ψ��(d��)�]�б��ľ�����ˮ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؎X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Ĭ�w�Y(ji��)���Լ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

 ��ӡ���(y��)
��ӡ���(y��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