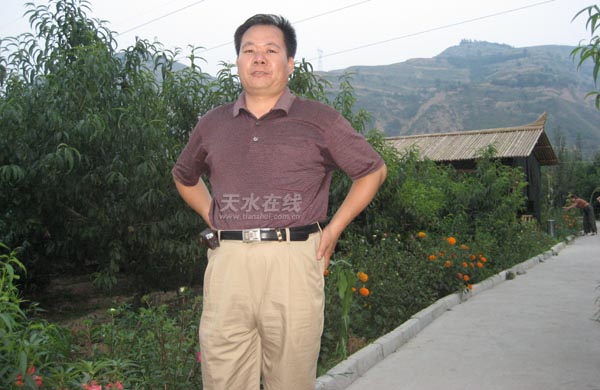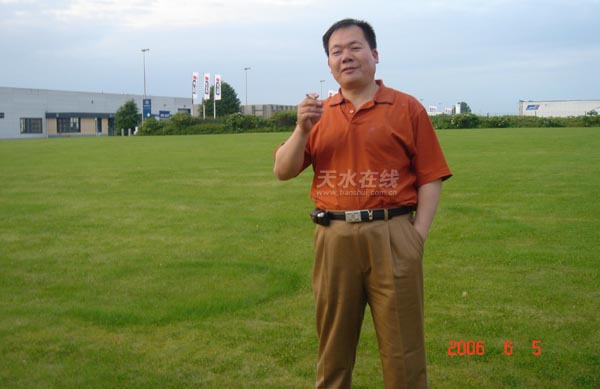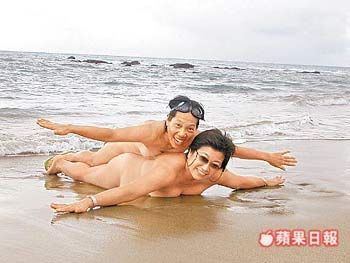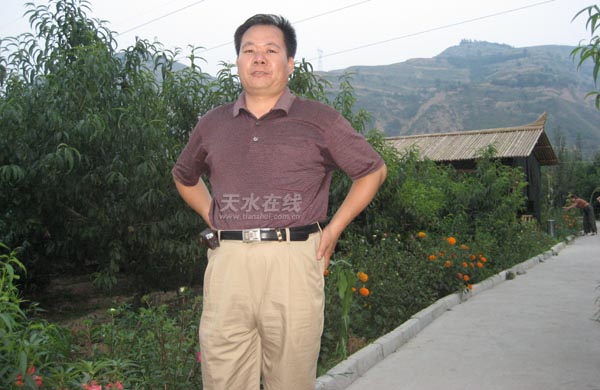
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ˮ�ھ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ēu�@������Ҍ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Ʒ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�ã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?q��ng)?b��o)����ˇ�ܿ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^(gu��)һƪС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}���顶������2005�����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ۜ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Єe�ڟo(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ӛס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ߵ����֡����؎X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l(xi��ng)Ұ��Ϣ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߿����ǁ�(l��i)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С�ұ����Ǻ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ӵ�С�f(shu��)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Ҳ��һ�N�ɺϰɣ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к�ƽ�^(q��)�e�k�x��(sh��)��(ji��)�Ļ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(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؎X���m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Մ�eֹ֮�g����ż����¶��һ�z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Ǐ��v��(j��ng)�L(f��ng)˪�����^(gu��)��Ę�Ń����Єe�����ĵ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۾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һ�l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l(xi��ng)Ұ�ĝh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^(gu��)��Մ��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Ը��C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n���l(xi��ng)Ұ֮�g���^(gu��)��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Z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ĺ�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Hӡ�C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Ƭ���r(sh��)�Ĵ��y(c��)����؎X߀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Єe��һЩ��ӹ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ߵ�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ͻȻ��(w��n)�ң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؎X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��ۂ�?c��)�����?ji��n)�����ǂ�(g��)�؎X�����п��xһ�°�����@ƪС�f(shu��)���ʼZ����(xi��)�ÿ��治�e(c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ġ���ƪС�f(shu��)��(b��o)���f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(sh��)Ԓ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Ԓ�Z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](m��i)�І����Ҍ�(du��)�@ƪС�f(shu��)�^(gu��)�ߵ�����ֵ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؎X�ġ���Ƭ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r(sh��)�Ŀ��⡣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һЩ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ġ��Ļ���͡�������ˮ�(d��ng)ǰ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Ј�(c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��w�й��w�(y��n)��ȡ����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ͬ�S�ӛQ��֮ˮ���͛](m��i)���ČW(xu��)ʥ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Ǯ�(d��ng)���o���ڕ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£��u�u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ʼZ�����ֵĽ�(j��ng)��֮�Е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҅s�y�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f(shu��)���ʼZ�����H��(xi��)�ô֫E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̵��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ѽ�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ʼZ��֮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С�f(shu��)����đ������ʹ���¶��˳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shu��)��ȡ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퍵��茑(x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ڮ�(d��ng)���茑(xi��)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У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һ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ի@��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؎X�@����ƪС�f(shu��)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Ү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һ���ի@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^(gu��)�ς�(g��)���o(j��)30����Ϻ���(sh��)�ֳ���ġ��Ї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(w��)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ӛ�d��ʼ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U�ʼZ֮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ǧ�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�Ų�׃���ɗl���v��(j��ng)�v���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ǧ�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v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ӵ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uŮ����֮���S����ؤ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ǵ���21���o(j��)���_(k��i)Ԫ�r(sh��)�ڵ��Ї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�U�ʼ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(w��)Փ���Ă�(g��)�Ƕ�ȥ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H��֮�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ڂ�ý���A���ˇ�(gu��)�˵�ٝ�u(y��)֮�⣬�Ļ������ߌ���{��ҕҰ�����侎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Ʒ��߀�ǂ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Ψ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؎X������{�넓(chu��ng)��ҕҰ�����(xi��)���@ƪ���ʼZ����С�f(shu��)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(l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؎X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ﴧ���l(xi��ng)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˲���ȱ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˲ŕ�(hu��)���@����ƪС�f(shu��)�ij��t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@�ӵ��ش��}�ģ�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ҁ�(l��i)�f(shu��)�Ǻ��y�{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ֻ�Є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(m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(c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ɞ�D�����ε��{(l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ǣ��؎X��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(k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ޱ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g��)��(��i)�����؞����С�f(shu��)��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Ƕ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ʾ�����{�S�ꂥ���}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ͨƪ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(m��i)��һ��蹦ힵµ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~�Z(y��)�����](m��i)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�߹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ڸ弈�ϔ[�_(k��i)�˼�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Z�ĸ�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Լ�ȥ���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ĵ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U���Z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ɰT�������^(gu��)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ò�ȥ�V�T�(y��n)�Z�T���е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Ĺ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ò�ȥ����ȥ��ُ(g��u)����ļZʳ�������еČ�(sh��)�ڟo(w��)�X(qi��n)�֟o(w��)�ܣ��㵽ɽ��R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^(gu��)�ǵ��(y��n)�Z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߃A (t��ng)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g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Ǜ](m��i)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߸����o(w��)����ī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؎X��(x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l��i)�s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ڌ�(du��)����Ľ^��(du��)ռ�С��eֵ��һ�����С�f(shu��)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(w��)Փ�Ǵ��L(zh��ng)�R���}(c��ng)�ͼZվ��վ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q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˹�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g�Ī�(d��)��hƈ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`���б��^��λ�Ŀ̮�(hu��)���@����Ʒ���Գɹ�����һ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Z(y��)�Ծ�����(ji��n)�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ĵ��Ț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q����߀�r(sh��)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{�Z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؎X��(d��)�ص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؎X��Ф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ǰ���w���ˣ����ǂ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顢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`�o�o�N�ڴ������nã����ϵ�Ѫ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@�ӵ����˶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ӵ���Ʒ��һЩ�������ČW(xu��)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ӠN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Ї�(gu��)�ČW(xu��)�L(zh��ng)���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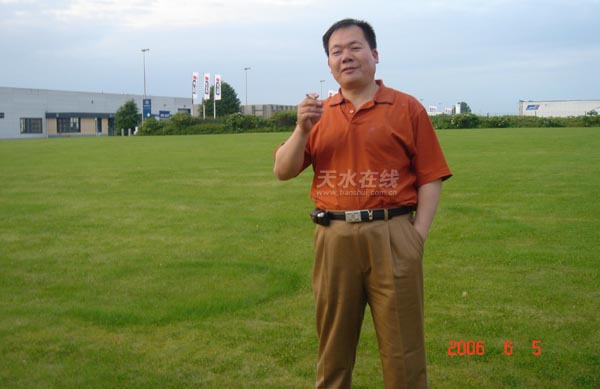

 ��ӡ���(y��)
��ӡ���(y��)